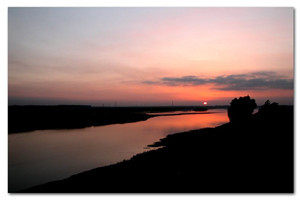乱世繁花
民国十三年,上海。黄浦江的汽笛声穿透薄雾,
将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城市从沉睡中唤醒。法租界的霞飞路上,
梧桐树的叶子刚抽出新绿,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路面,
溅起细碎的水花。街角的咖啡馆飘出浓郁的咖啡香,与远处寺庙传来的晨钟声交织在一起,
构成一幅独特的画卷。1、法租界内的丽都大剧院,
一场为赈济华北难民举办的慈善义演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后台化妆间里,
镜子擦拭得一尘不染,映出墙上挂着的各式戏服,五彩斑斓,流光溢彩。
林若渝坐在梳妆台前,身上穿着一袭月白色改良旗袍,领口和袖口绣着精致的缠枝莲纹样,
裙摆处巧妙地融入了西式剪裁,既保留了中式的温婉,又透着几分西式的灵动。
她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不久,一头乌黑的卷发被精心打理过,松松地挽在脑后,
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化妆师正为她描眉,她的目光却不经意间飘向一旁的化妆台。
一本牛皮封面的速写本静静躺在那里,上面压着一支削得尖尖的炭笔。本子微微翻开,
露出的页面上画着一幅场景:城郊的村庄,土地龟裂,草木枯黄,
衣衫褴褛的百姓们面黄肌瘦,在几个身着北洋军制服的士兵的刺刀威逼下,
扛着一袋袋粮食艰难前行。士兵们个个面目狰狞,
其中一个络腮胡士兵正抬脚踹向一个踉跄的老人,画面触目惊心。
这幅画线条简洁却极具张力,每一笔都饱***林若渝对军阀暴行的愤怒。她自幼在军营长大,
见惯了父亲林司令手下士兵的飞扬跋扈,只是从前年纪小,不懂这背后的黑暗。
留学法国期间,她接触了新思想,亲眼目睹了异国的民主与自由,再回头看祖国的满目疮痍,
心中便燃起了改变现状的决心。回国后,她表面上是热衷于社交活动的军阀千金,
实则暗中用画笔记录下这乱世的苦难,资助那些有志于救国的进步学生。“林**,
您的眉画好了。”化妆师的声音将林若渝的思绪拉回现实。她对着镜子微微一笑,
镜中的女子眉眼弯弯,眼神清澈,却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多谢。”恰在此时,
化妆间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身着深色西装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的西装剪裁得体,
熨烫得一丝不苟,衬得他身形挺拔。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双眼深邃而敏锐,
仿佛能洞察人心。他便是《沪江日报》的资深记者沈砚之。沈砚之刚走进来,
目光便习惯性地扫过整个房间,当他的视线落在化妆台上的速写本上时,脚步微微一顿。
那幅画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随即迈步走了过去。
林若渝从镜子里捕捉到了他的动作,心中微微一动。
她知道《沪江日报》最近一直在报道华北灾情,眼前这位记者,会是她传递真相的契机吗?
沈砚之走到化妆台前,仔细看了看那幅画,然后不动声色地将画册合拢。
他的指尖刚触碰到纸面,林若渝便缓缓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这位先生是?
”“在下沈砚之,《沪江日报》记者,前来采访此次义演。”沈砚之推了推眼镜,
语气平和地自我介绍道。“原来是沈先生,久仰大名。”林若渝站起身,微微颔首,
“我是林若渝。”“林**客气了。”沈砚之的目光落在她身上,“方才见林**的画册,
画功甚是精湛。”林若渝心中了然,脸上却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沈先生对绘画也有兴趣?
”沈砚之抬眸,对上她的目光,语气平静却带着深意:“林**画笔如刀,只是这刀太锋利,
容易伤着自己。”林若渝轻笑一声,从领口摘下那朵精致的白玉兰胸针,
胸针的花瓣温润细腻,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她轻轻将胸针塞进沈砚之掌心:“白玉兰的花期虽短,总好过做温室里的假花。
”沈砚之握着掌心的胸针,只觉得那香气仿佛能渗入心底。他看着林若渝意味深长的眼神,
点了点头:“林**所言极是。”林若渝转身走向舞台方向,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裙摆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沈砚之站在原地,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胸针,陷入了沉思。这场看似不经意的相遇,
却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舞台上,灯光璀璨,
林若渝的身影出现在聚光灯下。她弹奏着钢琴,悠扬的琴声在剧院里回荡。
沈砚之坐在观众席的角落,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的身影。他看到她指尖在琴键上跳跃,
看到她脸上专注的神情,心中对这位军阀千金的好奇又多了几分。演出结束后,
沈砚之走出剧院,外面已是华灯初上。法租界的夜晚格外繁华,霓虹灯闪烁,车水马龙。
他走到街角,正要叫一辆黄包车,却看到林若渝被一群记者围住。记者们七嘴八舌地提问,
大多是关于她的留学经历和未来打算。林若渝从容应对,言辞得体,既不显得张扬,
也不失风度。沈砚之没有上前打扰,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观察。他注意到,
当有记者问及林司令最近的动向时,林若渝的眼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黯淡,
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巧妙地转移了话题。待记者散去,林若渝正要上车,
无意间瞥见了站在街角的沈砚之。她对他微微点头,然后便上了汽车,消失在夜色中。
沈砚之看着汽车远去的方向,握紧了手中的胸针,转身融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2、《沪江日报》的办公室位于一栋老式洋楼里,楼外爬满了青藤,绿意盎然。办公室内,
弥漫着旧报纸和墨水的混合气味,墙上贴满了各种剪报和地图,
空气中都仿佛漂浮着新闻的气息。沈砚之坐在靠窗的橡木桌前,桌上堆满了各种资料和文件,
桌角的铜制台灯散发着温暖的光芒,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映在墙上那些关于华北灾情的剪报上。他手中捏着一张折叠整齐的字条,
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赈灾款流向可疑,林府书房或有线索。
”这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匿名信件,信封上没有任何寄件人信息。沈砚之摩挲着字条边缘,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义演后台林若渝那双清澈却藏着倔强的眼睛。他几乎可以肯定,
这封信就是她寄来的。华北灾情日益严重,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灾民饿死、病死的报道,
而**拨下的赈灾款却迟迟不见踪影。沈砚之追查了许久,却始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如今有了这条线索,他心中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终于有了突破口,
担忧的是林若渝的处境。她一个军阀千金,竟敢搜集父亲的罪证,一旦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喧闹的街道。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知道,自己必须谨慎行事,
不仅要揭露真相,还要保护好提供线索的人。与此同时,林府正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气氛中。
这座位于法租界的豪宅,占地面积广阔,庭院深深,雕梁画栋,却处处透着冰冷和威严。
林若渝的房间布置得精致典雅,墙上挂着她从法国带回的油画,
书桌上摆放着各种书籍和画笔。但此刻,房间里的气氛却异常凝重。林若渝坐在梳妆台前,
手中紧紧攥着一本薄薄的账本副本,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账本的纸张已经有些泛黄,
上面的字迹密密麻麻,记录着一笔笔粮食交易的明细。就在刚才,
她在父亲书房外无意间听到了父亲和粮商的电话通话。“王老板,
那批粮食务必在三天内运到,每吨抽成三成,少一分都不行!
”林司令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林司令放心,一定办妥。只是……最近风声紧,
那些记者盯得厉害。”粮商的声音带着几分讨好和担忧。“怕什么!在上海这片地界,
还没人敢动老子的人!”林司令冷哼一声,“灾民饿死几个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咱们的利益!”那些冷酷无情的话语,像一根根针一样扎在林若渝心上。
她冲进书房,将账本副本摔在桌上,质问道:“父亲!你怎么能这么做?
那些都是救命的粮食,是灾民的希望啊!”林司令正在喝茶,闻言猛地将茶杯摔在地上,
青瓷碎片四溅,有几片甚至溅到了林若渝的旗袍下摆上。
他怒气冲冲地指着林若渝:“老子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用点钱怎么了?
你个黄毛丫头懂什么!这乱世之中,只有权力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林若渝看着父亲狰狞的面孔,心中一阵冰凉。她从小崇拜的父亲,
那个在她眼中英勇无畏的军人,如今却变得如此陌生和可怕。她咬着唇,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转身退出了书房。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将自己关在里面,久久无法平静。她知道,
自己必须做些什么,不能让父亲一错再错,不能让那些灾民白白送死。3、深夜的法租界,
万籁俱寂,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和黄包车铃铛声。
一辆黄包车在僻静的巷弄里悄无声息地穿行,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轻微的声响。
林若渝坐在车上,用一件深色的斗篷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
她的心中既紧张又坚定,手心微微出汗,紧紧握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黄包车在一家挂着“笔墨纸砚”幌子的小店铺前停下。店铺的门紧闭着,
门口挂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在夜色中摇曳。林若渝深吸一口气,下车后轻轻敲了敲门板,
按照约定的暗号,敲了三下,停顿一下,再敲两下。片刻后,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穿着灰色短褂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警惕地看了看四周,低声问道:“要买什么?
”“请问有上好的徽墨吗?”林若渝低声回应“我要的是黄山松烟墨。
”这是他们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中年男人点了点头,打开门让林若渝进去。店铺里面不大,
货架上摆满了各种笔墨纸砚,但仔细一看便会发现,很多都是空盒子。
这里其实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中年男人接过林若渝手中的信封,
打开看了看里面的账本影印件和粮商的照片,满意地点了点头:“林**放心,
这些东西一定安全送到沈先生手中。”“多谢。”林若渝低声道,“请务必小心,
不要暴露身份。”中年男人将信封迅速藏进一个竹制笔筒里,
然后点了点头:“林**快回吧,这里不安全。”林若渝不再多言,转身走出店铺,
重新坐上黄包车消失在夜色中。斗篷的流苏在月光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仿佛是黑暗中的一丝希望。三天后,
沪江日报》的头版用加粗的黑体字刊登了一篇震撼人心的报道:《赈灾黑幕:权贵私吞善款,
百姓深陷水火》。报道详细揭露了林司令等人私吞赈灾款的罪行,
并附上了清晰的账本影印件和粮商的照片作为证据。报纸一经发售,便被抢购一空,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此事。人们愤怒地指责那些中饱私囊的权贵,为华北的灾民感到痛心。
林司令看到报纸后,气得浑身发抖,将办公室里的东西砸得乱七八糟。
他暴跳如雷地吼道:“查!给我查!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很快,
线索便指向了《沪江日报》的沈砚之。林司令当即下令,让宪兵队包围报社,
将沈砚之抓起来。报社里一片混乱,记者们惊慌失措,
打字机的声音和人们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沈砚之正在整理后续报道的资料,
听到楼下传来桌椅碰撞的声音和士兵的呵斥声,便知道出事了。
他迅速将账本原件塞进墙壁的一个暗格里,然后镇定地站起身。门被猛地踹开,
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冲了进来,为首的正是宪兵队的队长。
他指着沈砚之厉声喝道:“沈砚之,你涉嫌诽谤林司令,跟我们走一趟!”沈砚之没有反抗,
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我是一名记者,报道事实是我的职责。”“少废话!带走!
”队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沈砚之被宪兵们推搡着走出报社,外面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他看到报社的同事们担忧的眼神,心中有些愧疚,但更多的是坚定。他知道,
自己做的是对的,哪怕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宪兵队的审讯室阴冷潮湿,墙壁上斑驳不堪,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铁锈和霉味。沈砚之被绑在冰冷的刑架上,双手被粗糙的麻绳勒得生疼,
背上已经布满了鞭痕,渗出血迹,染红了他的衬衫。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
没有丝毫屈服的迹象。审讯官是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
他拿着一根烧红的烙铁,走到沈砚之面前,烙铁上的火星四溅,散发出灼热的气息。
“沈砚之,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是谁给你的证据?是不是林司令的女儿林若渝?
”沈砚之咳出一口血沫,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新闻记者的职责是揭露真相,
至于消息来源,无可奉告。”“嘴硬!”审讯官气急败坏地举起烙铁,
就要往沈砚之身上烫去。就在这时,一个士兵匆匆跑了进来,在审讯官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审讯官的脸色变了变,最终还是放下了烙铁,恶狠狠地瞪了沈砚之一眼:“算你运气好,
林司令有令,留你一条活口,查明背后的势力。”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审讯室。
沈砚之松了一口气,但身上的疼痛让他几乎晕厥过去。他知道,自己暂时安全了,
但危险并没有解除。他必须想办法出去,继续揭露真相。林府内,
林若渝得知沈砚之被捕的消息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眉头紧锁。
她知道父亲的手段,如果不尽快想办法救出沈砚之,他恐怕性命难保。“**,
您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吃点东西吧。”侍女端着一碗粥走进来,担忧地说道。
林若渝摆了摆手,没有胃口。她的脑海中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
她想到了父亲书房里的那本完整的账本,那才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拿到账本,
或许就能救出沈砚之。4、凌晨时分,夜色正浓,整个林府都沉浸在睡梦中,
只有巡逻的卫兵偶尔走过,脚步声在寂静的庭院中格外清晰。林若渝换上一身男装,
头戴一顶黑色礼帽,将头发塞进帽子里,脸上还沾了些灰尘,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厮。
她借着巡逻卫兵换岗的间隙,悄悄地溜到了父亲的书房附近。书房的窗户紧闭着,
窗台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林若渝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巧的***工具,
小心翼翼地撬开了书房的后窗。窗户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她屏住呼吸,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动静,确认没有人后,
才翻身跳了进去。月光透过窗棂照在地板上,形成一道道银色的光斑。
书房里弥漫着一股烟草和旧书的混合气味,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古董。
林若渝按照记忆中的位置,蹲下身,用手指轻轻敲击着地板上的地砖。